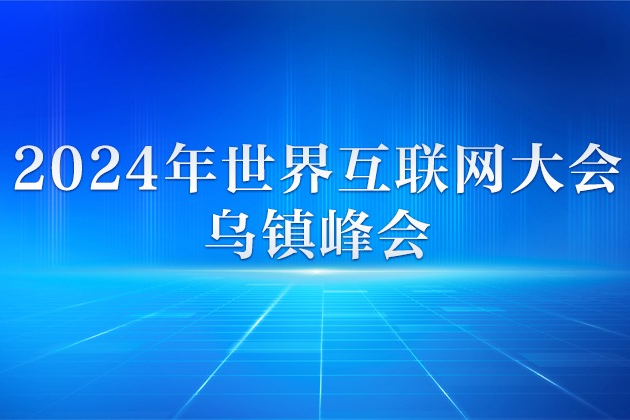编者按: 技术拟人化作为一种狭义且显性的人性化趋势,无论是从技术发展规律还是从人类需求来看均具有必然性,而“恐惑谷”效应为非人客体的拟人化进程设置了路障,成为技术拟人化发展的悖论。本文借鉴媒介环境学、进化心理学、后现象学等领域对技术拟人化的理解,分析技术拟人化趋势中存在的“恐惑谷”悖论,从中寻求理解人机关系的思路与适应技术拟人化的出路。研究认为,我们需把握技术拟人化适应人类需求的优势,通过减缓而非限制技术拟人化、回归具身经验的直接性、营造社交环境的可供性实现跨越“恐惑谷”的可能。
技术拟人化的发展演进经历了功能拟人、形态拟人、思维拟人三个历史阶段,分别从结构功能、外观形态、智能学习等不同维度逐步提升技术的拟人化程度。这三个发展阶段不同程度地对人类的技术认知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激发了对技术伦理的深度追问,如职业竞替、技术恐惧、情感危机等,酝酿着人机关系的深刻变革。当技术形态的拟人化程度接近人类却无法满足人类的拟人化期待时,“恐惑谷”效应将成为阻碍技术拟人化发展的客观心理因素,并进一步影响人机关系的良性发展。出于对该问题的反思,本文借鉴媒介环境学、进化心理学、后现象学等领域对技术拟人化的理解,分析技术拟人化趋势中存在的“恐惑谷”悖论,从中寻求理解人机关系的思路与适应技术拟人化的出路。
一、自限或自主:技术拟人化的悖论
智媒时代,拟人化智能机器人凭借功能的多样性从不同维度融入了人类的生活场景:播报新闻的AI虚拟主播、服务用户的智能语音助手、查询指路的导航机器人……这些智能媒介在外观形态、语音功能、互动模式等方面具备不同程度的人类特征。尽管智能媒介具有拟人化发展的趋势,但“如果拟真机器人设计师的终极目标是让机器人和人类保持完美的相似,那么仅就这一目标而言,恐惑谷很明显阻碍了我们通往成功的道路”。“恐惑谷”效应通过呈现人类对拟人客体的好感度变化,针对机器人的拟人化设计提出了限制性建议,为非人客体的拟人化进程设置了路障,成为技术拟人化发展的悖论。
(一)技术拟人化的“恐惑谷”效应
1970年,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政弘发文指出,随着非人客体(机器人)的外形与人类形象开始接近,人类的好感度将会增加;但当其与人的相似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人类反而会产生抵触与厌恶心理,好感度急剧下降;而非人客体的拟人化程度达到与真人几近无异之时,人类的好感度又将骤然回升,从而在坐标轴上形成一个起伏的“N型”山谷状曲线。且相较静态客体而言,动态的非人客体会加大曲线的斜度,加剧人类好感度的变化。该效应中的负面感知令人既恐怖又困惑,因而被称为“恐惑谷”。
对于恐惑感的来源与成因,心理学家恩斯特·延奇指出人的恐惑感源自犹豫不决时的不确定性。而弗洛伊德认为恐惑感源于人类自身已被克制或压抑的潜意识的复苏,是出于人类对超越死亡而达到永生的渴望。“恐惑谷”效应的提出令人忧虑非人客体的过度拟人化,同时也促使人们思考技术适度拟人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二)技术拟人化的必然性演进
拟人化在技术的发展取向与人类的认知期望上均存在一定必然性,其作为技术发展的显性特征在智媒时代尤其显著。拟人化的本质是将类人特征、动机、意图或情感灌输给非人类对象的想象或真实行为。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拟人化可以是一种过程,可以是一种倾向,也可以是非人对象本身的类人特性。因此,拟人化既是形态特征的演化,也是功能特征的演变,是一个无限趋近且永无止境的进程。拟人化是人性化的,而人性化并非都是拟人化的。可见,人性化是智能媒介的先行逻辑框架,而拟人化则是其后天发展趋势。
从社交心理的角度来看,人类本能地存在拟人化期望,技术拟人化存在合理性。情感功能的拟人化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人类的无意识社会反应,满足了人类的拟人化期望。与具体化机器人的互动对参与者来说是一种更具吸引力的体验。
二、危机与转机:人机关系中的感知波动
“恐惑谷”效应与技术拟人化的矛盾在于人类对拟人化客体好感度的骤降,理解这一矛盾需立足于“恐惑谷”效应中起伏波动的人机关系。“恐惑谷”之所以被称为“谷”在于其呈现出的非人客体的逼真性与人类主体的好感度之间犹如山谷般起伏变化的关系,随着非人客体逼真性的提升,人类好感度的下降与上升建构起一个动态的关系区间。其关系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从冷漠到好感度降低前的上升期,从好感度开始降低到好感度降至最低的下滑期,从好感度最低到好感度反弹的回升期。
(一)上升期:媒介技术的拟人化优势
“恐惑谷”效应中的上升期指随着机器人逼真性的提高,人类好感度随之提升的阶段,体现了技术拟人化在人类需求补偿方面具有促进人机关系的优势。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决定:1、媒介拟人化是对人类生理结构的补偿。保罗·莱文森指出,媒介技术的存活需全方位适应人类需求,尤其是生理层面的便利性。2、媒介拟人化是对人际社交缺失的补偿。是人类在经历一定时间的技术中介传播之后对前技术时代人际互动的诉求。
(二)下滑期:技术的他异风险与恐惑感知
“恐惑谷”效应中的下滑期指随着机器人逼真性的进一步提高,人类好感度骤降的阶段,其主要原因也有两个:1、好感度的下降源于陌生感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困惑和不安。2、好感度的下降源于对机器人的经验缺场。意味着拟人化经验的误差或匮乏将对人机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现实生活中,机器人可以说是最具他异色彩且最缺乏现实经验的技术人工物。其拟人化对人类而言需要调用大量前经验的联想,而当其拟人化程度达到外观接近人但行为与人不同时,则会令人类陷入经验悬置的困惑,从而陷入认知困境,并进一步影响了人类对机器人的正面评价。
(三)回升期:人机互动的临场感与情感优势
“恐惑谷”效应中的回升期指机器人逼真性超越某一临界点时,人类好感度重新上升的阶段,其意味着具身经验对强化人机关系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当拟人化的非人客体表现出对人有益或友善的特征时,人类对非人客体的好感度将快速提升。具身临场感能进一步发挥人机交互中的情感优势。移情作为传播过程中的要素通常被认为只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然而在现有的人机交互中已经出现了移情现象。它意味着机器摆脱中介属性,成为直接的交互对象,人与机器之间的临场社交才是人机交互的本质。因此,跨越“恐惑谷”的机器是理想的传播主体。
三、起点与终端:重塑拟人化认知的经验路径
“恐惑谷”中的动态人机关系凸显了技术拟人化设计对人类经验获取方式扬长避短的重要性。透过“恐惑谷”效应中的动态人机关系不难发现,经验是致使人类好感度变化的重要因素。作为人类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立身之本,经验拥有两个来源:其一,感官、知觉形成的观念;其二,内省、反思形成的观念。前者由个人的亲身经历构成,而后者则受到外部环境影响。据此,可将“恐惑谷”效应中的经验构成分为可切身感知的生物认知经验与受外部环境影响的文化认知经验,二者共同构成了恐惑感经验。
(一)“恐惑谷”的经验诱因
关于“恐惑谷”的生物认知经验,既有实验主要将其分为先天性本能和后天性习得两种。森政弘试图将“恐惑谷”效应解释为一种人类“自我防卫本能”的结果,这一点在进化心理学处得到了验证。除了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分析“恐惑谷”认知心理,亦有研究从感知期待的角度进行成因解读。人类拥有作为潜意识和应激策略的拟人化期待,从而抵抗陌生因素,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这一期待值依附于既有经验,若期待未被满足或客体的拟人化违背了原本的期待也将引发“恐惑谷”效应。这解释了为何拟人机器人的表情和行为与人类高度接近但又无法达到人类正常水准之时会产生“恐惑谷”效应:由于人类的拟人化期待是基于对人类生物体的认知经验而产生的,已经刻入潜意识之中,若潜意识与意识发生冲突则容易激发恐惑感。
人类的拟人化经验除了源于自身的感官体验,同样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如各类文学影视作品中均有关于机器人的拟人化呈现,建构并培养着人类对拟人化机器人的审美与认同。若一个机械体的形象“不够拟人”,其类人特征就会有明显的机械体征,从而容易辨认,对人的心理认知没有太大的影响;若一个机械体的形象“非常拟人”,其非类人特征就会成为人们重点观察的部分,进而给人心理带来奇怪的感觉,即人类好感度突然下降。
(二)拟人化经验的可获得性
从“恐惑谷”效应的成因来看,人的经验分为生物经验和文化经验两个维度,二者均存在被建构的可能。因此,除了限制技术的拟人化发展,经验的可获得性能够更好地应对技术拟人化悖论。
从现实应用入手,减缓技术拟人化的进程能够给予人类充分的时间和机遇获取更多的认知经验,以弥补人类对技术拟人化经验的缺失。从时间来看,拟人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完成时,尤其是人们对高级智能技术产品的可接受性更需要检验。减缓技术拟人化的发展进程并不意味着抑制其发展,而是为人类适应技术拟人化提供更广阔的时空,将特殊、陌生的经历上升为成熟、稳定的经验。
从人机关系入手,跨越“恐惑谷”在技术设计上应遵循以身体为出发点,实现对具身感知与具身情境的观照。跨越“恐惑谷”的设计应该将技术设计纳入人类的具身认知,一方面强化拟人客体的互动属性,互动本身有助于减少未知性,会克服本能的恐惧;另一方面培养人与拟人化客体的互动习惯,使人对拟人客体的感知形成于具身互动之中。唯有将具身经验与互动情境相结合才能在全面体知中获得完整的拟人化经验。
从悖论源头入手,跨越“恐惑谷”在技术上需要社会环境的配合。跨越“恐惑谷”在设计层面要求机器的拟人化特征提升至与人类近乎无异的程度,令人难辨真假。从“恐惑谷”成因的两个经验维度来看,以外形设计为切入点解决了生物认知经验层面的适应性问题,即感官适应。此外,更要在动态的交互能力上达到甚至超越人类预期,即环境适应。社交环境本身不仅为人类也为机器人提供了行动的环境条件,还促进了机器人动态社交的可能性,成为塑造机器“主体性”的环境经验,为人机相互适应提供了外部驱动力。
四、结 语
人性化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本身是技术不断适应人类的进化过程。而技术拟人化作为一种狭义且显性的人性化,无论是从技术发展规律还是人类自身需求来看,均具有必然性。在人工智能技术以人类为学习中心的前提设定下,智能机器人表现出日趋鲜明的拟人化色彩。然而,“恐惑谷”效应的提出为非人客体的拟人化趋势设置了路障,一度限制了技术拟人化发展,困扰着人类对拟人化客体的认知,成为技术拟人化悖论。“恐惑谷”效应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揭示了人在认知层面与拟人客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从“恐惑谷”效应解读智能技术中人机关系的变化将促进理解机器拟人化对人机交互的影响;其阶段性特征也意味着,人机关系在技术拟人化维度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理解人机关系不能局限于单一维度,需以辩证的眼光审视关系的动态变化。从“恐惑谷”的形成机制与动态的人机关系来看,经验是影响恐惑感的关键,通过减缓而非限制拟人化、回归具身经验的直接性、营造社交环境的可供性等方法使拟人化经验可获得,是实现跨越“恐惑谷”的适应性路径。
作者简介:
叶 立,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福建数字传媒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闽江学院新闻
传播学院讲师
林爱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4期,原标题为《跨越“恐惑谷”:基于技术拟人化悖论的人机关系审思》。原文15200字,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www-jsjc-gov-cn-1416.res.gxlib.org.cn:443/rwt/1416/https/NWZC675FNF6GT5SPPFZT6Z5QNF/s/6LKMQXg3-Maql_tNalr9Eg。